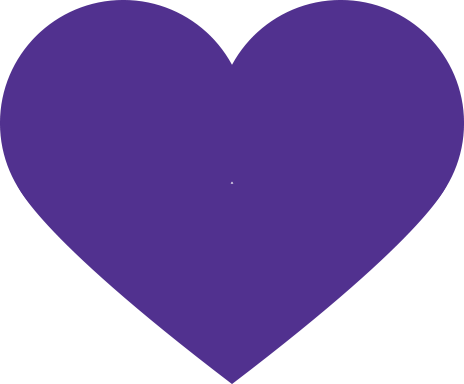
| 第三章 |
我的傅靖痕
虽然这个男孩又黏人又赖皮,
可我真是喜欢他。

我被我妈领到夏家的时候,据说夏云的亲妈刚死没几个月,我至今都记得夏云是怎样一脸倔强地拿着她妈妈的遗像挡在门口,像狼王守护着自己的领地那样同我们对峙的。她下巴扬得高高的,恶狠狠地说:“老贱货!带着你的小贱货从我们家滚出去!”
这场毫无悬念的对峙在彼此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很快就结束了。夏云被她爸爸硬拖着关进了房间,不论她如何声嘶力竭,几次想要扑上来将我和我妈撕碎,都是徒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是极为不屑的,我想,夏云这样的娇娇女,要跟我打架,玩蛋去吧!
很显然,夏云后来也对这一点有了深刻的认知,她身上青青紫紫的伤痕可以印证。
但是,她打不过不一定代表她就甘心。夏云很优秀,这从她屋子里大大小小的奖杯、奖状可以看出来。优秀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脑子是好使的,而夏云不仅脑子好使,脸蛋长得还漂亮。这种既优秀又漂亮的女生在学生时代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存在,因为她们拥有自己的团体,和一大堆脑残而又喜欢“路见不平”的粉丝。
所以,在我还没踏入夏爸爸安排的那所学校的时候,我的名声就已经在那里传开了。当然,那不可能会是什么好名声——
我那个时候活脱脱就是一个叛逆少女,打架、喝酒、抽烟,画又浓又夸张的妆,把校服剪掉,穿露骨的裙子在各种场所招摇……总之,但凡能惹夏爸爸跟我妈生气的事,我都特别愿意去做,并且乐此不疲。
我就是顶着夏云给我渲染的名声和一身夸张的打扮坐到傅靖痕身边的。因为发育得慢,那个时候傅靖痕的个子还没我高,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看见我时脸红得跟猴子屁股似的。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刚刚坐下的时候,我不小心看到你内裤了,对不起啊。”
我说:“没关系。放学后你给我等着,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就算给你白看了。”带着一口土气的地方口音。
小男生哆哆嗦嗦的,当场吓得脸都白了。
可那天我没能收拾他,因为我被夏云的各路粉丝堵在学校的废操场,打得很惨。等我一瘸一拐地回去,教室里空荡荡的,就只剩下傅靖痕一个人。
我想着我们好歹同桌一场,以后我逃课、抄作业肯定还得找这个小子,于是很友好地问候了一句:“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傅靖痕一句话就把我堵住了,他顶着他那张人畜无害的脸说:“你不是让我等着吗?”
我分不清他这是挑衅还是装傻,只是那种时候,我真觉得我就是想揍他。
“你别打我脸,我妈要是看到了,肯定得让你请家长。你……你就打我……要不你还是别打我了。”
“……”
我想,我的同桌真的是又傻又呆又好玩。
可是,傅靖痕一点都不傻,他的奖状、证书堆得比夏云的还高。主席台上他代表学生会发言的时候,那套又丑又肥大的校服居然还能被他穿出那么一点气质来,以至于学校一大堆女生都觉得他这朵鲜花插在我这坨牛粪上是多么浪费而又让人恨得牙痒痒的事情。
就因为这个,我还不待见过傅靖痕很长一段日子。我琢磨着,座位又不是我找老师安排的,凭什么我要因为这个小白脸被人指指点点?
傅靖痕笑嘻嘻地说:“夏果,挨着我坐有什么不好的?你开小差被老师点名时我可以给你递字条,笔记我帮你抄,作业我帮你写,连你裙子被撕破了我都可以把校服借给你遮挡,你还不乐意个什么劲儿啊?对了,我还可以教你普通话。你把你那口乡村音改改吧,我有时候真听不懂。来,跟着我念:傅靖痕、痕痕、阿痕……”
我一拳过去,他就立刻消音,效果特别好。
整个初中,就在夏云时不时给我使点绊子、傅靖痕偶尔犯贱非要找揍中慢慢地过去了。
毕业的时候,傅靖痕跟只树袋熊一样死皮赖脸地挂在我身上:“夏果,夏果,我真舍不得你!我知道你也特别舍不得我!要不我让我爸给你开个后门?”
他爹是一所高中的校长。那学校特别好,但凡A市的学生都削尖了脑袋想往里钻。夏云比我高一届,她考上那所学校那年,夏爸爸高兴得跟嫁女儿一样,大摆筵席。
就冲夏云在那儿,我压根不想瞅那学校一眼,何况就我那成绩,估计夏爸爸花再多的钱,学校也不一定敢收我。我把傅靖痕甩开,说:“拉倒吧!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我想,我可真是讨厌傅靖痕成天顶着他那张与世无争的娃娃脸装疯卖傻。他明明知道,要不是为了他说的那些条件,我早八百年就换座位离他远远的了。
最后,夏爸爸还是给我找了一所不错的高中。虽然那所学校不能跟傅靖痕他爸的那所比,但以我的成绩,把我弄进去也算是十分费工夫的事了。
我从来没想过会跟讨人厌的傅靖痕再有任何交集,他代表新生演讲的时候,我都没把他认出来。
这小子过了一个暑假跟打了激素一样疯长,整个人拔高了一大截不说,脸上的婴儿肥也不见了,眼镜被摘下来,露出又高又挺的鼻梁和微微上挑的凤眼,大约是处在变声期,说话声音又粗又哑的,我能认出来才怪。
所以,我在学校走廊上被傅靖痕热情地熊抱的时候,脑子还有点反应不过来。他说:“夏果,找你可真不容易。你那些又短又暴露的裙子呢?你的唇膏呢?你的假睫毛去哪儿了?咦,你也发育了,这两块软绵绵的。你在几班啊?”
我抽不死他!
可比我都高出一大截的傅靖痕还真不好抽,于是,我只能勉强推开他,冷冷地说:“傅靖痕,你装什么疯、卖什么傻呢?我跟你有那么熟吗?你不知道我有多恶心你吗?跟牛皮糖一样甩都甩不掉!你以后离我远点,否则我见你一次抽你一次!”
初中升高中那年夏天,我把被染得乱七八糟的头发染回来了,还把那些陪着我招摇过市、穿起来又冷又不舒服的裙子也打包通通扔进垃圾箱,因为我妈说:“你不是嫌我脏吗?你不是觉得用我的钱、住我的地儿糟蹋你了吗?我告诉你夏果,就你这样,以后一辈子都得靠着我,一辈子都得跪着求我养你!你就庆幸你是从我肚子里钻出来的吧!要是换成夏云,就是跪着,我也不一定理她。”
我第一次觉得,为了早点离开夏家,我得付出点什么。
我的同桌自然不会再是傅靖痕,她叫姚倩,开学第一天就顶着一头火鸡似的头发、操着一口地道的地方口音问我:“来根烟不?”
那个时刻我愣了一下。我想,当年我出现在傅靖痕面前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样醒目且让人猝不及防。
姚倩说她家是挖煤的,围在她爸身边的明星、模特数都数不清,一群女人成天在她妈面前招摇,她恨不得抽死她们;
姚倩说她柜子里的LV、Hermes堆得快发霉了,问我们要不要,她给我们弄几个来;
姚倩说她爸买了直升机,问我们星期天要不要跟她去玩;
姚倩说……
姚倩的谎言漫天飞,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就像一个既蹩脚又专业的小丑那样为大家制造各种各样的笑料。她得意扬扬又漏洞百出地炫耀着自己不拥有的一切,她虚伪、做作、懦弱、可笑,她被全体女生唾弃、攻击都能梗着脖子、红着脸跟人狡辩半天。
可是,我一点都不讨厌姚倩,甚至某些时候,我觉得我跟她有那么点同病相怜。
我从来不懂得跟这些富家子弟相处,这就好比夏云热衷于各种钢琴、小提琴比赛,而我乐得在KTV里晃着小腿点着啤酒当麦霸一样。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像真正的亲姐妹那样彼此拥抱、安慰、分享。
姚倩后来才哭着跟我讲,她妈在镇上开一家文具店,她压根就没见过她爸。她好不容易才从镇上考上这所学校,把她妈乐坏了,恨不得马上把那文具店搬过来陪着她。但她一口拒绝了,因为她不想让别人看不起她。
我像我奶奶小时候拥抱我一样拥抱了她,那可真是一个难度颇大的姿势,因为她那会儿胖得跟头猪似的。我既别扭又紧张,第一次这样心疼一个人。我看着姚倩在我怀里哭得歇斯底里、抽搐不止的时候,就像看见当初我妈突然花枝招展地出现时,躲在奶奶怀里一脸戒备而又懵懂的自己,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姚倩的感情都特别微妙。我弄不清楚自己帮她、安慰她、心疼她的时候是真心地为了她,还是仅仅为了自己。
我不知道姚倩是什么时候跟傅靖痕搭上线的。在开学那天我把傅靖痕狠狠得罪一遍扬长而去后,这小子一直没在我面前出现过,我甚至以为他已经乖乖回他爸那儿去了。
傅靖痕那天仍然嬉皮笑脸的:“夏果,想我不?我最近可愁了,我爸知道我来赵伯伯这儿,差点把我打死,门儿都不让我出。我可真是想死你了!”说完他就扑上来占我便宜。
我本来想一掌把他拍飞来着,可是这小子窜得老高,我发觉把他一掌拍飞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于是就只能把他推得远远的。我说:“滚!”
我想,我是真心讨厌傅靖痕的。他就像夏天里的向日葵那样,金灿灿的,热烈又招摇。他活得那么坦荡而且天真无邪,以至于他一出现,我就觉得刺眼。
傅靖痕不休不止地缠了我整整一个夏天,我每次把他推开,他都能跟八爪鱼一样迅速黏过来。他总是喋喋不休地数落道:“夏果,你这是过河拆桥。当年你的作业是我给你做的吧?卷子是我给你抄的吧?你裙子坏了,我还给你补过一回来着。对了,你第一次来大姨妈,还是我在网上查了教你怎么弄的呢……”他如此这般,每每都能轻而易举地挑起我的怒气。
我不得不绕着他走,可他总有办法把我找出来。他成功地让姚倩为他当牛做马,甚至连我报了一个素描班,他都能神出鬼没地出现在那个培训班上,像只苍蝇一样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那段时间,我真是想了一千种方法把傅靖痕弄死。
可一旦姚倩问我为什么那么讨厌傅靖痕时,我一个字都答不上来。
姚倩一边啃着鸡爪,一边含混不清地嘟哝,要是有个男生能像傅靖痕对我那样对她,她早八百年前就减肥了,然后漂漂亮亮地跟他谈一场天荒地老的恋爱。她的话让我突然就对傅靖痕产生了那么一丝愧疚感。
我那个时候就隐隐觉得,对傅靖痕产生愧疚感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果然,傅靖痕后来变本加厉。
他从姚倩那儿知道我要补数学,就成天拿着一本习题围着我转。他说:“夏果,你不是要补数学吗?我帮你!我帮你!不收钱!”
我一打架,他就大惊小怪地冲上来,什么乱七八糟的跌打酒都往我身上抹。
连我每个月痛经,他都能备了热水袋跟红糖水,高调地跨过我们之间相隔的班级给我送来,弄得全校都知道我每个月是哪几天。
我总是在“忍不住想抽死他”和“羞愧于自己居然想抽死他”这种微妙的感觉里徘徊。
如果不是那年傅靖痕的妈妈过世了,我想我一辈子都不可能承认自己喜欢他。而如果我知道自己后来那么喜欢他,我也一定不会在那个夏天既矫情又懦弱地刻意躲着他。
高二的时候,他妈妈自杀,他一夜长大。
我从来没见过那个样子的傅靖痕,这株骄傲而又招摇的向日葵瞬间枯萎。他在消失整整一个星期后出现,满脸胡茬地抱住了我,一句话也没说。那是唯一一次我忘了把傅靖痕推开,因为,这个少年汹涌而来的悲伤仿佛夏天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一样瞬间笼罩住了我,我几乎都以为他哭了。
可是,傅靖痕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他曾经清澈明亮的眸子像冬天早上的大雾一样朦胧而沁凉。他一脸憔悴地跟我说:“夏果,我不能陪你了,我得回我爸那儿去了,以后可能还要出国。我本来还想陪你一直画画来着。”
他说完掉头就走,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抱住了他。我想,这个男孩,虽然他那么黏人,又赖皮又高调,可我真是喜欢他。
我真是,那么那么的喜欢着他!
我把自己从回忆里抽出来的时候,窗外已经变得漆黑。夏雨躺在他天蓝色的小床上睡得既香甜又安静,他长长的、卷卷的睫毛柔顺地伏在眼睑上,小巧而又挺挺的鼻子呼吸安稳而轻柔。我忍不住凑过去吻了他一下,我想,他可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子。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念傅靖痕,想得自己胸口发疼。那会儿我刚把夏雨接过来,他安安静静的,什么话都不说,可是一见我躺在床上发抖,他就跟一只小狗一样跑过来吻我的脸,小小的、安静而又倔强的一张脸上,一双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清澈的眸子静静地注视着我。
莫医生说是我帮助夏雨挺了过来,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是夏雨治愈了我。
我帮夏雨把被子盖好,然后轻轻走出了房间。林家大得跟酒店一样的宅子让我突然没来由地觉得一丝森冷,走廊上那些被外界估成天价的油画仿佛中世纪的死尸一样冷冷地窥视着我,我打了个寒战,小跑着奔回房间。
我想,我可真是讨厌这样的房子,它冰冷得像是古代帝王们为自己修建的陵墓。
我把自己吓得一回房间就关了门,还没喘过气来,回头就见消失快半个月的林越深一言不发地坐在床沿,床头台灯的微光将他让我一度羡慕嫉妒的脸照得泛着白光。
那效果——我腿一软,吓得差点当场跪下。
“去哪儿了?”林越深扭开身边的开关,松了松领带,将他修长的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眼睛一眨,目光就幽幽探了过来。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还是觉得一阵后怕,一边颤抖着腿慢慢挪着步子,一边故作轻松地答道:“哄夏雨睡觉呢!”
我刚走过去,就被林越深扯进怀里,他身上淡淡的酒气毫无预兆地扑鼻而来。今儿林越深肯定喝醉了,不然不会这么反常地碰我。他舌尖滑过我耳垂的时候,我条件反射般地跳了起来。
一跳起来,我就知道坏了,肯定惹他生气了。果然,我发现林越深脸色黑黑的,于是我赶紧指着浴室解释说:“我还没洗澡!”然后就跟只兔子似的冲了进去。
浴室里,我抱着腿坐在地上。我想,不是今天,不能是今天,今天我没法跟林越深生娃。
一想到傅靖痕,我压根就没办法面对林越深!
我颤颤巍巍地把手上的纱布扯开。伤口早就结痂,好得差不多了。我用牙齿咬上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哭了,眼泪跟不要钱一样拼命往下掉。我想:可真是痛,太痛了!
眼泪和伤口流出的血液混在一起,又咸又腥,我哆哆嗦嗦地一边小声抽噎着一边将伤口咬开,又害怕被林越深听到。我就是觉得疼,特别疼,可是不知道是从哪里开始疼起来的。我好像压根找不到原因,于是就只能哭了,仿佛那样就能少疼一点似的。
我走出浴室的时候还在想,林越深不会碰我。他有洁癖,只要一看见伤口上的血,肯定一点兴致都没有了。他有那么多女人,他那么有钱,今晚想去哪儿都行,没必要非得是我,我只会坏了他的兴致。
可是我一出去,林越深就恶狠狠地盯着我,漆黑的眼睛像狼一样发出幽幽的光。我不知道他今晚是怎么了,一点都摸不透他的情绪。我本来还想演一下,大惊小怪地跟他说我是怎样在浴室里摔倒然后把伤口碰到的,可是还没等我开口,他就一反常态地吻住了我。
不,那怎么算是吻呢?他咬我,霸道而愤怒,好像我是他的杀父仇人似的,我的嘴唇都被他咬破了。然后他的舌头强势地扫进来,堵住我的呼吸,等他把手指从我睡衣下面伸进来的时候,我真是吓住了,条件反射般地去推他,而他把我反手按在墙上,像一匹狼那样快速而凶猛地冲了进来。
那真是屈辱的姿势。身体干涩,我觉得那里肯定裂开了。我发了疯似的去咬他,尖叫道:“放开我,林越深!”
林越深不为所动,他的动作凶猛而蛮横,他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腕,仿佛恨不得把它们捏碎。我的睡袍被他撕开,然后,我像条死鱼一样被他重重丢在床上。他抓着我的手腕,恶狠狠地说:“怎么,我碰不得你?”然后冲进来。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样羞耻,老太太将我贬低得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将自己卖给林越深的时候,甚至是夏云指着我骂我是小贱货的时候,我都没有觉得这样羞耻过。这种羞耻感让我哭着咬他,对林越深拳打脚踢,可我所有的反抗对他来讲都不值一提。
他被欲望染得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仿佛一定要将我弄死,不死不休。
傅靖痕,救我!我听见自己在心里呐喊,然后绝望。
直到双方筋疲力尽时,这场情事才结束。我蜷缩在被子里,满脸湿润,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我心惊胆战,一动也不敢动,害怕林越深还会再扑上来。
我几乎一夜没能入睡。第二天一早,我听见林越深起身走掉后,才敢进浴室清洗。
我看见镜子里我的身上布满青青紫紫的痕迹,一张脸苍白憔悴。
我觉得自己像具死尸。
我在水里泡了一个多小时,非常困倦,可是我偏偏无法入睡。我多希望自己能够睡着,然后醒来,发现一切都只是一场梦,我爸我妈没有出事,我没有跑去跟林越深求婚,而傅靖痕也没有出国。
我愿意睡死在高中的那个夏天,连风里都有傅靖痕的气息,他的笑容既温暖又明亮,他的手掌有世界上最温暖的触感。
一出浴室,我就看见去而复返的林越深。他西装笔挺,全身上下没有一丝褶皱,头发被梳得一丝不苟,一如当年我第一次见他时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模样,可我下意识瑟缩了一下。
林越深将一杯水和药递给我:“吃了。”声音没有任何起伏。
我惊恐地看着他——这药我见过,我刚跟林越深结婚那会儿,我就偷偷吃过。我那会儿根本不是真的想嫁给他,更别说生孩子了,所以,通常第二天我都会偷偷吃一颗这样的避孕药。
我条件反射般地退了一步。
在浴室里我已经跟自己做好心理建设,我想,没什么,就当林越深抽风好了,没准儿他这一抽抽出个娃来,那我就再也不用被老太太逼着喝那些恶心的东西、去做检查了。
可是,他现在要我吃这玩意儿!
他不想要我生的孩子!
“我不要!”我将脸别到一边,抓着浴巾的手握得紧紧的。
林越深轻轻地笑了,那笑容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凉薄而危险。他喝了一口水,然后将药含在嘴里,在我还来不及躲避的时候,找到我的唇,撬开牙关,哺过来。
我下意识挣扎,去踢他、推他,可他的进攻像昨天一样凶猛而快速。他几乎是直接咬开我的唇,势如破竹般将那玩意儿往我嘴里送,直到确定我真正吞下去后才放开。
他一放开我,我就跑进卫生间里,想将那玩意儿抠出来。我想我得快点怀上孩子,我不要再被林越深碰。我愿意一辈子活在这个金丝笼子里,可不代表我愿意像个妃子一样任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有那么多女人,他那么脏,他爱找谁找谁,但不要碰我!
林越深抓起我的手腕,轻而易举地将我整个人提起来。我怒气冲冲地瞪着他:“你是个疯子!有病!浑蛋!”
“你不是喜欢吃这玩意儿吗?”林越深捏着我的下巴,逼着我与他对视,浓密而漆黑的睫毛下,他的眼睛冷得像深潭,“怎么,现在改变主意了?”
我又惊又怒地盯着他——他怎么知道我以前吃过避孕药?
不,不!他这样的人,他这样习惯掌控一切的人,有什么不知道的?
他还知道什么?
我脑袋里轰的一声炸开,无数我曾经忽略过的东西像洪水一样涌来。如果林越深什么都知道的话,如果他什么都知道……
“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要你生孩子吗?”林越深含住我的耳垂,声音低沉,仿佛情人间的呢喃,可是下一句就彻底将我推入深渊,“因为,我怕他一生下来就是个野种!”
我像一块被人啃过的棉花糖一样蜷缩在床上,从玻璃窗照射进来的阳光懒懒的、明晃晃的。夏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钻进我怀里的,他亲了我一口,然后就安安静静地盯着我,也不说话。
金色的光线一寸一寸吻着他小小的脸、眼睛、鼻子、嘴巴、睫毛……我想,这可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子。
如果……如果那个孩子生下来了的话,应该也跟夏雨一样吧。
其实,我跟林越深是有过一个孩子的。我这个人又懒又没什么记性,避孕药也不是每次都能记得吃。大概是结婚一年的时候吧,我发现自己吃什么都想吐,一检查就发现肚里多了个小东西。
我吓得要死,谁都不敢说。那时候我爸妈贪污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他们压根就没空理我。老太太也不待见我,再加上我爸妈的事,整天对我横鼻子竖眼睛的,恨不得我快点跟林越深离婚。而林越深那阵儿特别忙,我睡着了他才回来,我醒来时他又走了,总之,我们俩根本见不到面。
我又慌又怕,觉得自己都是个小孩呢,怎么养一个娃啊。我也想过打掉,可医生说头胎如果不要的话,以后再想要就挺难了,况且,经常吃避孕药也不是什么好事。
那段时间我六神无主,简直跟缕游魂似的,成天做些乱七八糟的梦。偏偏那个时候,傅靖痕找到了我。
我跟林越深一结婚,就完全将傅靖痕屏蔽,手机、MSN、邮箱……一切可以联系的方式统统换掉,全部交给我妈去处理,我甚至连分手都没有亲自跟他说过——我舍不得。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傅靖痕跟个疯子一样,找了我整整一年。
直到我妈在电话里说:“夏果,让他死心。他连你们家住址都查到了,如果闹到你们家,让越深和老太太脸上不好看,我跟你爸这回就真的没救了!”
我把手机掼在墙上,摔得粉碎。
我们约的见面地点是一家咖啡馆。我那天的妆将脸画得很红润,打扮得特别招摇,估计光手上那枚婚戒就能闪瞎一堆人的眼。我一进去,还没坐下就开始跟傅靖痕道歉,我笑嘻嘻地说:“对不起啊傅靖痕,真的对不起!我以为我妈都跟你说清楚了呢,没想到你找了我这么久。什么事啊?”
傅靖痕像被雷劈了一样,震惊地看着我。他咂了咂嘴,过了很久才吐出几个字:“夏果,你怎么了?”
我摊了摊手:“什么怎么了?哦,你说我结婚的事啊。是,这事我是对不住你,可你不是出国了吗?你一出去就是一年多,怎么谈恋爱啊?我以前喜欢你不就是因为你随时都在我看得见的地方吗?你一走,我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需要你了。”
“夏果,不是这样的,你……”傅靖痕颤抖着伸手过来握住我的手,他的手瘦得跟只剩下骨头似的,脸色白得像鬼一样。
我反手把他的手握住了,特别真诚地打断了他,我说:“傅靖痕,你真的是个挺好的人,真的。我也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我以前小,不懂什么是爱情,总觉得有个人天天黏在我身边就是爱。可是我现在结婚了,也懂事了,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幸福,我现在就觉得,每天能在我男人臂弯里醒来,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了。”
“你……爱他?”傅靖痕绝望地问。
“嗯!”我幸福地点点头,然后走过去,将他的手放在我腹部,说,“傅靖痕,看在我跟你关系那么铁的分上,我跟你分享件事。我怀孕了,医生说有两个月了,我都兴奋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没告诉我老公呢,你给我提提意见呗,我该怎么告诉……”我还没说完就被人泼了一脸的果汁。
姚倩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指着我的鼻子就开骂:“夏果,我真是瞎了眼才认识你!傅靖痕找你找得都快疯了!你知道他是休学回来找你的吗?你说的都是些什么狗屁!”
我立马就怒了:“姚倩,关你什么事?你抽什么风呢!”
姚倩作势就要上来抽我,她气得一双眼睛红红的,像是恨不得扇我两巴掌,傅靖痕死死拉住她,她才没得手。
我从桌上抽了纸巾擦拭脸上的果汁,冷嗤了一声:“不就是分个手吗?搞得自己要死要活的。既然大家谈不拢,那么以后我们也不要见面了。”一说完,我转身就走。
我走得飞快,死死攥着自己的手掌,嘴唇都咬破了才忍住没有回头。我特别害怕自己一回头就忍不住扑进傅靖痕怀里让他带我走。
你会遭到报应的,夏果!你这样伤害他,一定会遭报应的!我跟自己说。
一出咖啡厅,我就瘫在我妈怀里,身上全是冷汗。我妈的脸色也变了,她问:“夏果,你怎么了?”
“肚子……肚子痛。傅靖痕,我疼。”
我妈把我送到医院,然后就知道我怀孕了,乐得跟什么似的。她说:“夏果,这回妈妈可有救了!你肚子可真是争气!快点打电话告诉越深啊!”
我当时瘫在病床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听我妈这样说就想笑。我还真笑了:“呵呵,你得意什么啊?我也没说要这个孽种啊,生下来干什么,跟你一样以后把他卖了吗?”
“夏果,你胡说什么呢!我告诉你,你跟越深那是结婚,是明明白白、正正经经地办了结婚手续的。什么孽种不孽种的?别成天开口闭口胡说八道。我现在就给越深打个电话。”
“这孩子要不要我还不知道呢,但是你现在要是敢把电话拨出去,我就敢立马把孩子做了!”我没什么力气,说话声音也小,但我就看不惯我妈那副得意的嘴脸。
“你……”我妈气得当场摔门而去。
我其实也只是吓唬吓唬我妈,我没想过要打掉孩子。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全是傅靖痕,一想到傅靖痕,我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我整个脑袋里都是傅靖痕那张既憔悴又难过的脸,回家后我就把自己扔在床上,任眼泪哗啦啦地淌。我觉得眼睛疼、心脏疼、肚子疼,浑身都疼。
我没想到报应会来得那么快——在我还没有真正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先一步离开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