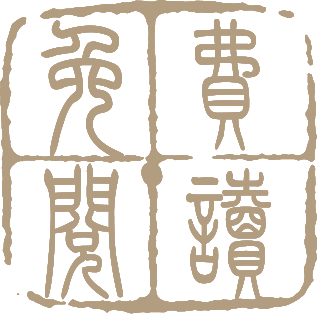
一握髯与四粒齿
——育温·台·波尔多的传说
解题
据盖倍尔(Gerbert)说,这个优丽的传说,是十三世纪所作的东西。但今日我们所传的,乃是较印刷术发明稍前时所写。这篇故事,诏示了以国民的历史为基础的英雄传说和冒险故事间的推移。
这个传说的优丽的趣致,显然引起了人们的感兴。巴奈斯公(Lord Berners)在亨利三世(Henry Ⅲ)时代,把它从法文释成英语。到了近世,有许多诗人挥着彩笔,对这绝妙的好诗加以润色。维兰特(Wieland)的最美的诗歌之一,是这个传说;魏倍尔(Weber)的出色的歌剧之一,也是这个传说。还有,大诗人莎士比亚(Shakespear)把阿倍隆(Oberon,育温传说中的人物——译者)的故事织入在《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里面,成了在虚幻中浮出来的艳丽的花形。
育温(Huon de Bordeaux)所访的巴格达(Bagdad),在传说上也被叫作巴比伦(Babylon)并且被想作这两者是同一个都市的名字。中世纪的作者,屡次不顾地理的事实,因此这种谬误,也无足深咎。
在育温的传说之中,妖精是时常出现的。欧洲中世纪的传说,通常多为妖精的信仰所润色。然而像育温的故事那样,和该信仰有密切关系的东西,究属不多。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其次,应该注意的,是育温的传说在某种事件上,和阿尔托尼德(Ortnit)的传说显然有相似的地方。因此,我们知道在前者(法兰西的故事)和后者(日耳曼的故事)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某学者唱说育温传说的一部分,是从《英雄传》(Helden-Buch)中的阿尔托尼德的故事里采取来的。可是,如果《英雄传》的出版和写作育温的传说都在十三世纪,那么,这学说的可能性,不能不说是很少了。
不过,据盖倍尔说,阿尔托尼德的传说,是在九世纪已经存在了的,所以,《英雄传》中的阿尔托尼德的故事本身,即使不是育温传说的蓝本,我以为也可以推断前代的阿尔托尼德的故事,是这个美丽的法国故事的蓝本。
那么,这两个传说的类似点在哪里呢?在育温的传说中,阿倍隆(Oberon)给了育温种种的助力;在阿尔托尼德的传说中,爱尔倍梨契(Ellberich)替阿尔托尼德做了许多事情。特别是,阿倍隆和爱尔倍梨契,是丝毫无异的超自然的存在。何以呢?因为不必有待于语言学上的研究,也可以知道Oberon是将Ellberich稍稍变化了一下的形象,这是类似的第一点。
其次,阿倍隆替育温拔下了巴格达国王的齿和髯的事件,使我们想起爱尔倍梨契为阿尔托尼德将叙利亚(Syria)王的髯拔下的事件来,这是类似的第二点。
复次,阿倍隆诰戒育温和他的妻,在罗马举行结婚式以前,不要有卑劣的行为;爱尔倍梨契也将同样的训戒给与了阿尔托尼德夫妇,这是类似的第三点。
再次,从大体的结构说起来,育温和阿尔托尼德都得了某种超自然的存在的助力,把国王的女儿夺来做了妻子,这是类似的第四点。
从这些事实推论起来,可以断定育温传说的一部分,是从阿尔托尼德的传说脱化出来的。
正文
(一)
从前,育温(Huon)和他的兄弟基拉特(Gerard)占领了波尔多(Bordeaux)地方。他们二人因愿称臣于武威赫赫的夏莱曼王,向巴黎出发。途中遇到一个像是贵公子的年青武士从草丛中跳出,突然向二人刺来。因为事出突然,未曾提防到的缘故,基拉特被他的利刃刺死了。可是,那青年也因敌不过育温的敏捷,仆在地上了。这个年青的武士,就是借了父亲的借势,做着放荡的行为,使有心的武士皱眉的夏莱曼王的王子萧罗德(Charlot)。
育温还以为只是打倒了一个无名的乱暴者,泰然到了夏莱曼王的宫庭。可是王子的悲惨的死耗,早已传到了王的耳际了。王竖起了怒髯,宣布育温的罪状,说是如果不将非常困难的冒险好好成遂,当作诚心向王忏悔弑戮王子之罪的证据,那么,育温的生命便不能赦了。所谓非常困难的冒险是:到巴格达(Bagdad)去把驸马的头颅斩下来;和回教皇(Sultan)的公主接吻;再把回教皇的灰色的髯的一握和美齿四粒拿回来。
育温是惊惶失措了,然而知道拒绝不得,就悄然到罗马探访法王(是育温的叔父)去了。
法王坐在华丽的高座上,耽于瞑想之中,一看见育温到来,便静静地举起眼来看他。在那秋水一般澄清的眼中,历历地映着缠在育温心中的苦恼。育温也一一诉明了心事,求谨严的叔父的援助。
法王在严厉的言辞中,夹杂着无限的慈爱说:“育温啊,一切都只有神明知道哩。”
育温在那简短的话中,得到了说不出的慰安。他靠着神的庇护,向迢远的东方——巴格达赶路。
最冷清的一天,育温在森林中迷失了路。他看天快到夜了,只管策马疾奔。然而,蔽空的老树接连到很远,露着非把这个焦灼万状的旅人囚禁起来不可的神气。不久天是完全夜了,他从马上跳下,只手执着缰绳,踉跄地沿着暗路走去。突然有一道微光,鬼火似地透过了树枝,隐约地闪烁起来,他喜欢得心跳了,便穿过茂林,拼命地向前驰奔。
俄而火光鲜明可见了,火是从一个大洞中漏出来的。育温大胆地闯进洞去,只见一个强壮的老人,在火旁蹲着。他的令人看了毛发悚然的长毛,蓬松地覆蔽了庞大的躯体,宛如野兽一般。
育温走到老人的旁边,用一点点自己所记得的那地方的方言向老人说话,可是,大概因耳聋的缘故,老人不曾回答一句。育温以为是由于自己辞令拙劣所致,尽是反复地说。老人只耸了肩,向他微微一笑。
育温弄得焦灼起来,发怒似地用本国语说了二三句,那个一直哑子似地沉默着的老人,忽然用了同样的语言,滔滔不绝地说话了。经过暂时的问答以后,育温知道这个老人,便是自己父亲的仆人盖拉斯梅斯。在意想不到的异境之土,而且是在无人往来的山奥的洞穴之中,竟邂逅了父亲的仆人,育温是吃惊于这个奇缘了。
盖拉斯梅斯在数年前,被在巴格达极尽骄恣的回教皇掳去。但他只是日夜憧憬故乡的苍空,所以瞒着别人的眼睛,逃到森林中来了。他将两三年来孤居在洞窖中的苦况向育温备述一遍。
育温专心一志地倾听着盖拉斯梅斯的遭遇,有如往昔的故事一般,他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声。他又询问到巴格达去的路径,盖拉斯梅斯大大地睁开了眼,暂时沉默着。大概是几年来的不可思议的遭遇,像络着的丝似地在一缕缕从胸底里引出来吧。不一会,他回答说:“到巴格达去的路有二条:一条是长得令人倦乏,一条是异常的短。长的一条虽然容易使人疲惫,但在不识途径的旅客,却是条平稳的路;短的一条,是穿过了不可思议的森林,一口气就可到达巴格达的。然而,在不可思议的森林之中,有着许多危难,在伺候冒险的人们。”
年青人的血液中,是有着弹力的。育温听了老仆的话,决心想到那条短的路上去冒一冒险了。盖拉斯梅斯觉得即使加以阻止,也是徒然,便默默地遵从了年青主人的意思。两人预备天一亮就离开洞窖。
过了几天,两人走到不可思议的森林中来了。盖拉斯梅斯不觉胆怯起来,不敢走在前头。育温则泰然踏进了森林之中。一千年来未尝闻到过人的气息的老树,吃惊似地发出幽声,将积在枝叶上的露珠,从暗空中摇落下来。盖拉斯梅斯惶恐地跟在主人后面走去,竟觉得森林中的巨石正在和老树攀谈、点头,它们大概是对于这意料不到的人的足音吃了惊,在发怒吧。年老的它,连宁静的心也消失了,在微暗的树叶缝中,时常鲜明地可以看到异样的东西,但忽而又像那消灭在暗黑中的电光似地消失了。不知育温有否看到,他只默默地策马前进。
他们走进了森林的深处,到倾斜的坡路上来了。当在高出空际的老柏树下憩足的时候,一座华丽的宫城,幻影似地映在两人的眼前了。他们失神地向它眺望着,黄金的门忽然无声地开开,眩眼的光从门内漏出,辉煌地照彻了四周。这时,有一辆被豹拉着的白银车,轧轹轧轹地出来了。戴着金冠的神一般的形姿,被灿然的光包围着,端庄地坐在车上,这是妖精王阿倍隆(Oberon)。
好像被人用冷水从头上浇了一下似的,盖拉斯梅斯不觉把身子缩紧了。一会儿,他用手拉住了育温的马辔,奋力想把它拉转后面。
育温俯视着他,静静地问:“做什么?”那是很低的声音。
盖拉斯梅斯气喘喘地回答说:“公子!怪物来了呢!你是最要紧的。”
“不要耽心!把手放了,把手放了呀!”
育温有点焦急起来了。然而盖拉斯梅斯一味只是紧紧地拉住了辔子,达达地拉向后面驰奔。他好像觉得自己的头颈如今已被可怕的东西攫住,拼命在森林中狂奔。育温骑在马上,只是发呆着。可是老人的苦心,也并无效果。
阿倍隆悠悠地取出了象牙的笛子,放在唇边。当高而尖锐的声音透过林中时,林中忽然黑暗起来,连黑白也辨别不出了。电光冲破了黑暗,纵横闪耀,好像有生命的东西一般。暴风摇动森林时,老树发了怒,狮子似地怒吼起来,倾盆的大雨,联合了自由无阻的猛风,威胁他们。
他们闭住了眼,只管在黑暗中行走,遂到了一座森林边境的小庵。盖拉斯梅斯怀了不安的心情,和主人一同在庵里休息了。他觉得好容易才从怪物的魔术中逃遁出来,仰视着逐渐放晴的天空,释然吐了一口气。这当儿,一辆白银的车缓缓移动着,好像行空的浮云一般。那个他以为再也不会遇见的阿倍隆的形姿,忽然重复映在他的眼前了。他跳了起来,好像被梦所魇的人一样。
可是,妖精王的面上,并没有现出怒色来。他在雪一般白的手里,握着一根百合的茎,端然坐在白银车中。一串系在象牙笛上的珍珠的索子,在柔滑得好像大理石搓成的项颈里垂着。他用纤指弄着小笛,静静地和凡人交谈。因为他对于育温与盖拉斯梅斯的无礼的举动感到不快,借了象牙笛的声音,呼唤狂风大雨的先前的怒气,而今已完全消释了。不过,他的话语,在柔和中确实是含着莫可言状的严厉的。俄而右手缓缓一动,将象牙的笛子放在唇边时,发出奇异的芬香来,在四周漂漾;同时,妙乐的声音也就响起来了。
盖拉斯梅斯忘记了自己的衰老;许多尼姑忘了峻严的习惯,欣然伴着音乐跳舞起来。只有育温把嘴紧紧地闭着,不曾稍微张开一些。
不久,阿倍隆将百合花在空中挥舞起来,音乐忽然止了。盖拉斯梅斯和尼姑,都突然平静了,好像从甜梦中醒来一般。
阿倍隆取出一只金杯来,赠给育温,并且说:“义人将美酒注在这杯子里,邪者千万不要用唇去触它!用唇一触,红酒就会变作火焰,把身体烧成灰烬的呢。”
妖精王更将系在颈上的象牙的笛子解下递给了育温说:“把笛子轻轻地一吹,人们听了它的声音,就会跳舞起来。便是千百个挥着冷得和霜一般的利刃的武士,也会忽然丢了利刃舞起来的。只要笛声不止,他们是会尽管跳舞下去的哩。如果想遇到我的话,那就把它很响地吹吧!虽远在千里以外,我也能比电光更快地到来的。”
说毕,阿倍隆即将百合花在空中挥舞起来。忽而,他的形姿幻影似地消失了,只有幽香淡淡地留着好像未尽的梦一般。
(二)
育温欣然接受了妖精王的赐物,鼓起勇气,与盖拉斯梅斯一起急急地赶路。一到茨尔蒙特,那地方的领主听到了不可思议的金杯的风闻,请求着育温,强要用唇去触那只杯子。“邪者千万不要用唇去触!”这是阿倍隆的训戒。在杯中盈浴着的甘酒,果然一霎时就燃着,烧去了那为罪恶所沾污的领主的嘴唇。
狐狸一般的领主却包藏着愤恨,设宴款待育温。兴酣的当儿,一百多个武士都奉了领主的命令,跳了起来,一齐拔出利剑,亮晃晃地有如霜夜的黄茅一般。然而育温毫不惊惶,他从容地把不可思议的笛子含在唇边,用了春风般柔和的气息吹着。武士们的脸上立即浮了欣色,丢了利剑作出姿态很可笑的跳舞来了。
育温乘隙和盖拉斯梅斯一同逃出了宴席,急急地赶路,向某巨人的城堡而来。这巨人曾从阿倍隆那里,偷去了不可思议的指环。将这只指环套在指上的人,是不会被凡人的剑所伤的。巨人靠了指环的魔力,以放纵的行为,犯了许多难赦的罪恶。
育温快到巨人的城堡时,一个骑士突然来到他的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了敬礼,说:“看到了先生的尊容,我就特地跑了过来,因为有一件事想拜托先生。”
育温惊讶地看着那骑士,问道:“什么事?如果是某所胜任的……”
骑士把事件向育温详述了一遍,说是他的未婚妻,被巨人夺去,虽然觉得愤懑也无可如何,因为敌不过指环的魔术,只好忍辱含垢着。
育温是个仁慈的人,一听到这情形,立即承诺了骑士之请,要去把少女拯救出来。
育温潜入巨人的房里来了。巨人因喝得酩酊大醉,死人似地酣睡着,在老松的树干一般的巨人旁边,垂了头若有所思的少女,大概就是那位骑士的未婚妻吧。
育温进去,使少女吃了一惊。他使她镇静了,急忙把事件的详情诉明。少女喜出望外,用焕发的眼睛向育温注视了一会,便慢慢地走到巨人旁边,从他可怕的粗大的手中,盗取了指环,递给育温。育温将它藏在怀里以后,即把挂在壁上的厚重的盔甲取下,披在身上。
这当儿,巨人突然张开眼睛来,把身子一摇,小山似地挺立着;育温和巨人,立即开始激战起来。
巨人被育温用手推倒了。育温将少女交给了骑士,仍和盖拉斯梅斯一起急急地向目的地前进。喜欢描写英雄儿的冒险的中世纪的作者,在途中设了种种的危难,磨折育温。但因有千篇一律之嫌,便从略了。
为贯串故事的情节起见,只要记住下面的二桩事件便够了。有一夜,育温梦见阿倍隆将一个娟丽的少女介绍给他,说她便是他未来的妻子。这时梦就醒了。
还有一件事是:有一天,他救了一个被狮子所袭几至丧命的男子。那男子非常无礼,不但不思图报,反将他的马偷了逃走了。育温和老人在后面追赶上去,向着巴格达疾驰。
(三)
不久,育温到了巴格达了。街市中许多人忙迫地往来着,到处都现出紧张的气象,所有的旅馆,都已被客人住满。育温与盖拉斯梅斯一直走去,寻到街市的尽头,好容易才找到了一个小客栈。
他们在这个客栈里,认识了一位老妇人,惊讶地询问街市何以这样热闹?
老妇人答说:“因为回教皇的女儿莱琪亚和赫揆尼亚(Hyrcania)王摆皮庚结婚的时期快到了,所以街市立即闹热起来。不过,公主对于这次结婚很不愿意。因为有一晚,公主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变成了犬,被摆皮庚在林中追来追去,正当喘有气,向四方逃窜的时候,忽然有一辆被豹拉着的白银车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东西,发着灿然的光,乘在车上;后面站着一个金发的、漂亮的年青骑士。在车上发光的那个东西举起右手来,静静地一挥,公主就回复了本来的面目了。
那东西看着公主,严厉地说:“这位年青的骑士,便是公主未来的丈夫呀!”
这样说了以后,那个虽然可怕,却饶有兴趣的梦,便像风筝的线一般断了。莱琪亚公主透视着弥漫全室的暗色,追逐留在眼睑中的残梦的踪迹。她似乎觉得年青的骑士,在黑暗中披着黄金做成的头发。从这夜起,公主的心狂乱异常,以致引起了宫娥们的注意。老妇人这样地向育温一直讲到深夜。原来,这位老妇人便是某宫娥的母亲。
育温倾听着老妇人的讲述,失神得差不多连呼吸都忘怀了。他想,车上发光的东西,是妖精王阿倍隆无疑。那么,天命注定娶公主的,恐怕就是自己吧。
育温对老妇人说;“公主是决不会做摆皮庚的妻的。”
老妇人听了育温的话,不觉吃了一惊,因为他好像是在断定自己的运命。不知什么缘故,老妇人竟觉得这位青年就是梦中的金发骑士。
天一亮,老妇人就到宫中去访公主。那时,莱琪亚公主在房中露着愁容,正在做结婚的准备;一看到老妇人,就睁着无力的眼向她看。她用了焦急似的口气说:“公主呵!梦中的金发骑士是……”
“梦中的金发骑士……”
公主打断了老妇人的话,把同样的话反复说了一遍。
老妇人慌忙接着说:“有一个年青的公子,宿在妾的家里,恐怕就是那位骑士吧。”
公主的眉头,稍微动了一下。
老妇人一一向她讲述育温的事。
公主叹息一会,就离开自己的房间,走进大厅去了。父亲回教皇摆皮庚以及许多大臣,都在那里并坐着,因为快要举行公主所不称心的结婚式了。
* * *
翌朝育温很早就醒来了,他偷偷地穿上了撒拉逊风的衣服,独自潜入回教皇的宫中。来到大厅的门外,最先映在他的眼中的,是面上长长地垂着灰色的胡须的回教皇。在回教皇的左边,傲然环视着一座的那个男子,恐怕就是新郎摆皮庚吧。
当育温的眼光从回教皇移到这个男子身上时,他不觉吃了一惊。原来这个男子,便是由他拯救了临危的生命,毫不感恩,却反把他的马偷了逃走的恶徒啊!
育温跳了起来,立刻走进大厅中去,从腰里取出偃月刀一挥,新郎的头颅就离开身子,落在地板上了。同时,育温的头巾也滚下来,金发卷了个旋涡,蓬乱地披到肩上。
莱琪亚公主像被妖怪所吸引似的,只是目不转睛地盯视着育温。
这当儿,育温突然走到公主的面前去,在雪一般白的额角上吻了三次以后,从怀里取出那只不可思议的指环来,快捷地套在公主的细小的指上。在比花更美的公主的面颊上,立即泛起红潮来了。
这些都是一瞬间内的事情,所有在座的人,用惊奇的眼光睨视新郎迸出血来。因了这意外的奇事,茫然呆立着,好像疯人一样。当他们执了剑站起来时,育温的那只指环,已被套在莱琪亚公主的纤手上,灿然发光了。
当护卫回教皇的武士们一齐拔出利剑,想直取育温的当儿;美妙的笛声,便在大厅的空气中漂漾起来。武士们的心,好像因温柔的春风兴奋起来似的,不自觉地丢了剑,手舞足蹈了。那勾人灵魂的笛声,渐渐传播开去,想把一切都吸引了去。武士们尽管舞着,在笛声未曾停止以前,他们非继续跳舞下去不可。
育温一面继续吹笛,一面将眼光落在莱琪亚公主身上,似乎在向她示意:“如果爱我的话,那么请和我一起出去吧!”
灵敏的公主领会了那意思。育温把笛子放在唇边,握着公主的纤手,悄然走出大厅去了。一个宫娥跟在他们后面。一座的人们,心中只觉得惊奇。他们受了笛声的魅惑,已没有向他们追赶上去的气力了。
盖拉斯梅斯站在宫外,拉住了几匹骏马的缰绳等候着。一看到育温等三人到来,熟练的老人,便立即扶公主和宫娥上马。这时,育温重复回到大厅去了。在大厅里,回教皇和武士们都因跳舞得疲乏了,张着朦胧的睡眼,在地板上躺着。
育温走到回教皇的旁边,叮咛地说明了来意,请求给他一握髯与四粒齿。回教皇立即勃然大怒起来,他想:“这家伙幻影似地跳进大厅来,不但杀死了新婿,夺去了自己的爱女,且敢冒犯王者的威严,前来乞取髯与牙齿,真是何等无礼啊!”
回教皇站起身来,厉声喝道:“左右!把这个混账东西拿下斩了!”
武士们一齐鼓了勇气,重复向育温刺过来了。育温向后退了一步,把那只不可思议的笛子尽力一吹,忽然天震地动,妖精王阿倍隆被雷电包着,在大厅中出现了。阿倍隆把用右手执着的百合一挥,回教皇和武士们的眼睑立即沉重起来,落在酣睡之中。
当育温走到回教皇的身边,想拔取髯与齿的时候,阿倍隆阻止了他,说可以回去了。
阿倍隆使育温等坐上了自己的白银车,送他们到亚斯卡兰(Ascalon)港。在那里,有一艘船奉了阿倍隆之命,为送育温等人到法国而伺候着。育温遵从了阿倍隆的意思,弃了马,和莱琪亚公主、宫娥以及盖拉斯梅斯一同乘在白银车上。
育温到了亚卡斯兰港,挽着公主的手,快要乘上船上去的时候,妖精王给了他一只金篮,篮中放着一握髯与四粒齿。不一刻,那船载着英俊的骑士和娟丽的少女,就将静静地在波上驶行了。
阿倍隆坐在白银车上,严厉地说:“年青的骑士呀!在罗马的法王为君和公主举行结婚式以前,切勿互相把清白之身沾污了啊!破戒者必有重罚。”
育温恭恭敬敬地俯了头,异常感谢阿倍隆的竭尽心力的爱护。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阿倍隆的车,早已不见了。
(四)
船载着那充满了春一般的希望的年青骑士,尽管驶行。到了敕颁多(Lepanto)的时候,育温叫盖拉斯梅斯移乘在快船里,为的要他先走,将金篮呈给夏莱曼王。谨严的老人,虽然让年青男女留在后边,觉得有点儿不放心,但为育温所迫,无法可想,只好移乘在快船中出发了。
育温和盖拉斯梅斯告了别,因在船中无所事事,恳请一个牧师为莱琪亚施了洗礼,将她改名埃曼达公主。牧师劝他接着举行结婚式。育温想起了阿倍隆的训诫,起初是不去听他。可是年青的他们俩,被热烈的恋情燃烧着,不能自持,因此只好烦牧师给他们俩举行仪式了。
育温破了妖精王的峻严的训诫,心中颇感不安,仿佛觉得可怕的灾殃已向后追迫过来似的。天快晚的时候,忽然狂风大作;倾盆的大雨,从漆黑的空中下落。育温似乎感到阿倍隆眼中冒着怒火,在云端凝视着自己,不觉得从心底里颤栗起来。
舟子们不晓得这个情形,误以为这意外的暴风雨,是由于海神的愤怒而起。为消释海神的怒气起见,由抽签来决定谁做牺牲,跳下海去。船上的人怀着愁绪,轮流着抽签,不久就轮到育温了。育温晓得不祥之签一定会落在自己身上,但毫不惶恐,过去抽了一根,那根不祥之签果真落到了育温身上。
当签落到育温身上时,公主仿佛感到陷入深渊去了。她面色变成苍白,颊上垂了泪,目不转睛地看着育温。育温露出依恋、苦闷的神色,向公主看了一眼,突然站起身来,跳到怒涛中去了。
这当儿,白影闪闪地黑暗中一动,公主也追随着育温,跳下海去。等到船上不见了二人的形姿时,暴风雨忽然止了。
两人漂到了一个岛上。育温为要去找寻食物,叫公主留在海边,独自走到山路上来。走下山谷时,在细流的旁边,望见一轩茅舍了。育温分开了繁茂的葎草,轻轻地叩门。低声应着出来开门的,是一个年老的隐士。育温叮咛地把自己的遭遇备述了一遍,求隐士与以援助。瘦得和鹤一般的隐士,皱起了白而且长的眉毛,热心地倾听育温的讲述。等育温讲完了以后,她便用了沉静的声调说:“既已破了妖精王的严戒,那就只有一个法子可以赎罪。请日夜一心不乱地苦苦修行,把所有猥亵的心思焚个净尽!并替埃曼达公主建一座矮小的茅舍,叫她在那里过清白的日月!”
育温乃自遏了骄傲的心,羊一般柔顺地依从了隐士的话。他筑了一座矮小的茅舍,叫公主住在那里面,自己则闭居在隐士家中,度其戒律峻严的日月。
岁月如流,公主住在山奥里,被冉冉飘驰的云笼闭着,连鸟声也不常听到,心情十分烦乱。她并不想回到那安居在宏丽的王宫的往昔去。从微暗的山路上,折东屈西地走到一个洞窖的旁边来时,她忍不住想睡了,遂在柔软的草上躺下。不一会,美丽的妖精们,不知从哪里像在春风中飞舞的蝴蝶似地婀娜出现了,在公主的旁边绕了一个圈子,坐在草上。在圈子的中央,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妖精们颊上浮了嫣然的笑,和孩子玩耍。
公主偷偷地站起身来,想看一看孩子的容颜。忽而妖精们的形姿消失了,肤色白皙的孩子,静静地睡在公主的怀里。这是神祗为要慰藉幽居僻地的孤寂,赐与埃曼达公主的。
没有多少时候,隐士寂然死在茅舍之中,育温和公主都失了无限的力了。他们之所以舍了人世的快乐,过着异常无聊的生活者,原是因为希望靠了隐士的高德之力,有解除阿倍隆的忿怒的一天之故。他们俩失了隐士,觉得每天的修行苦得不堪。
当他们俩的胸中涌起惰念来时,阿倍隆的妻子泰伊忒尼亚暗将那孩子偷去,带到妖精国里来了。这是因为她恐二人不久将陷入罪恶,不欲使孩子清白的心为所沾污之故。然而,他们俩自从失了他们视若生命的孩子以后,便在山野间呼喊、哭泣,日夜向四处找寻,好像疯人一般。
不一会,公主走到海边来了。这时,有一群海盗,从船里看见艳丽的公主从树荫里出来,便拥至她的旁边,想把她拖到船里去。
育温听到公主的哭声,拼命疾奔过来。一看到几个野蛮的男子用全力簇拥着弱不胜衣的公主时,他竖起了金发,向海盗们打去,有如跳到羊群面前去的狮子一般。可是,因他曾苦苦地修行了好几年,腕力也衰了;他虽拼命击过去,也并无何等效力,却反被绑在老树干上。海盗们遂扬着哄声,把公主簇拥到船里去了。育温奋力挣扎着,悄悄地从颊上流下热泪来。
阿倍隆虽然心肠很硬,但看了这伤心的情景,心也软了。他回顾那些侍在自己左右的妖精,叫他们去援助育温。妖精们在空中翱翔起来,来到育温的身边,割断了缚绳,将他扛着,越海过岭,迅疾得如电光一般。一到突尼斯(Tunis)某园丁的屋外,妖精们便悄悄地将育温放在门口。育温舒适地睡着,恍然感到如在漠漠的云中行走。
(五)
盖拉斯梅斯在敕颁多离别了主人育温,日以继夜地只管赶路,不久就到了夏莱曼王的宫城了。他用手把高高耸峙着的门扉轻轻地一叩,守门的武士问他是什么人,有什么事?盖拉斯梅斯把育温的伟业详述了一遍以后,说是自己奉了育温之命,把一握髯与四粒齿带来了。
武士将此意传达给王,但王并不轻易相信,因为他觉得将那在有名的巴格达称雄的回教皇的髯割下,并拔取了他的牙齿,这决不是人的事业;育温的使者,实在是可怪之极。于是下旨在育温亲自来到宫庭,拿出确凿的证据来以前,永远不要开门。
盖拉斯梅斯没法可想,只好悄悄地转回罗马去了。因为他打算到那边去等候育温。在等待中,长长的两月已经过去了,育温的形姿,却不曾在罗马出现。盖拉斯梅斯悟到必有什么灾难临到二人身上了,遂变了装,扮作流浪汉的模样,到处漂泊。
当他到了突尼斯的时候,偶然碰见了埃曼达公主的宫娥。他从宫娥口中,听到育温和公主已投海而死,她则已被卖到这里做婢女来了。盖拉斯梅斯仿佛觉得脚已陷入深渊,连路也懒得走了。他逗留在突尼斯,做了领主的管花人。
有一天,盖拉斯梅斯无意中把门开了。怪极!这位老人总以为育温已经溺死,孰知竟安静地在门口睡着。他跑过去,把育温摇了起来。育温因这意料不到的重逢,觉得非常欢喜。他把过去的遭遇详述了一遍,盖拉斯梅斯竖了肩,对于从主人嘴里漏出来的话,无论哪一节,都热心地倾听着。
* * *
却说海盗们将埃曼达公主簇拥到船上以后,立即离开了岛,把船桡到大海中去了。当桡过突尼斯的海面时,阿倍隆就起了暴风雨,把他们都沉在海底,只使埃曼达公主流到了海边。公主的美丽姿容,惊动了突尼斯那地方的人们,风闻远播开去了。
领主把公主召到自己的宫里来。公主因饱尝了忧患,面容已瘦得有些惨然。领主为她的容姿所动,热烈地求她做他的妻,然而公主只冷然把领主回看了一眼。留在眼睑里的那个年青的金发骑士,纵使在死的世界里,也仍是她的丈夫啊!
在此刻,公主对别的男子连话都不愿说,她铁石般顽硬地拒绝了领主的要求。可是领主每天只是同样的愿望逼迫公主,颇有在未与以答应以前,求婚决不中止之势。
育温绝不知道这事,他帮盖拉斯梅斯做管花的卑微工作,借以排遣胸中难堪的愁苦。领主的女儿看了育温的凛凛的姿容,燃起热烈的恋情来,时时用了甘言蜜语,想感动育温。然而,育温自从失了埃曼达公主以后,觉得人世好像灰块一般,只要用手去一碰,就会崩坠下来的。他烦厌似地不听少女那种甜蜜的话,领主的女儿,在心里暗暗怀恨着。
不久,埃曼达公主的宫娥,知道公主并未溺死,不料就起卧在同一宫中。她连忙将这事告知育温,于是,在育温的心中,涌起暖和的血潮来了,好像死了的灵魂突然苏生过来似的。育温猛然站起身来,决意要拼了命,去把公主夺回来。
懂得爱情的少女,是很能理解男子的心的。领主的女儿,看到近日育温的行动有点异样,觉得很奇怪;暗中探听它的原因,遂知道了育温与埃曼达公主的关系。这时,她燃起了怒焰,发誓非把这个可憎的男子杀掉不可。于是,她向父亲谗言,那个管花的青年男子,便是觊觎领主性命的恶徒。
育温被绑缚了牵到领主的面前来。这位受了莫须有的罪名的金发骑士,闭住了眼睛沉默着。这时,有一个少女气喘喘地跑了进来,那是埃曼达公主;因为她从宫娥那里,听到了育温身子的危险。公主崩坠似地在领主面前跪了下去,只管替育温乞命。领主顽硬得好像铁石一般,他怀着峻酷拒绝自己的热恋的怨恨,且嫉妒其和别的男子的相爱,乃冷然地拒绝了公主的恳求说:“公主!如果公主答应做某妻子,某就饶他性命。否则,今天即将处以死刑。”
领主卑怯地利用了公主的柔弱,想逼迫她与自己结婚。公主却觉得连听到那种话,也是不洁的。她在苍白的面上,浮着难移的决心的神色说:“那么,你是怀着无论如何非把育温弄死不可的心思么?”
“不消说得!”现在,领主也变成断然的了。
“如果这样,那么,妾也跟了一起到冥府去吧。”公主断然地说了,紧紧地把嘴唇闭住。
俄而,育温和公主被绑在大柱子上了,柴薪在他们俩的四周,山一般地堆积着。领主命兵士燃起火来,猛火伸了红舌把柴舐着。当它发出焰来,包住他们俩的时候,盖拉斯梅斯和宫娥号淘大哭起来。
恰巧在这一刹那,白银车幻影一般地在空中出现了,在车上发光的东西举起手来,向他们一招,育温、埃曼达公主、盖拉斯梅斯以及宫娥,忽然成了车上之人了。领主和警卫的武士们,茫然仰视着天空,好像疯人一般。不一会,车便悄悄地分开了白云不见了。
在白银车上发光的东西,不消说,是妖精王阿倍隆了。因为他为育温与埃曼达公主的热烈的爱情和悲惨的不幸所感动,遂乘了白银车,来救他们的性命的。那个可爱的孩子,在妖精国里天真烂漫地游戏着。公主用双腕紧紧地抱住了那孩子,滔滔地流下欢喜的泪来。
(六)
有一天,在夏莱曼王的宫中,举行隆盛的比武大会。骄傲的骑士们,有的拿着磨亮了的盾,有的拔出锐利的丈余的长枪,交起锋来。夏莱曼王坐在高座上,津津有味地看着比试的盛举,他的眼睛,被一个刚才进来的覆面骑士吸引去了。
那个覆面骑士,蹴着强壮的马腹,肋下挟了长枪,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枪头一动,有的在大腿上被它刺了一枪,脱出了铠子;也有在马背上一滑,不觉坠下地来的。虽然遮着面幕,认不出是哪一个骑士,但因在他白银的鍪兜上插着羽毛,在空中飘扬,所以在许多骑士之中,王只注视着他。
不久,比试完毕了,王特地把覆面骑士召到身边来。那骑士从容地走了过去,毫无一点惶恐的神色。一个如花的少女,跟在他的后面。满座用了低声喃喃私语起来,好像风吹落叶一样。当骑士把足停在王的面前时,王用了虽然低微,却很有力的声音说:“是哪一个,给朕看惊人的武艺的?”
骑士默默地去了面幕,蓬蓬的长发,在苍白色的额上波动着。当余发向后由肩胛落到白而发光的盔甲上时,骑士用了凛凛的声音说:“是育温。”
满座露出惊奇的神情来了。王觉得给他看出心的震撼来是失策的,所以故意用了沉静的声调说:“叫卿做的三件事,做得怎样了?”
“那三件事已圆满地成功了。现已把篮子带了来,当作证据。”
王取了育温捧着的那只金篮,静静地将盖揭开,只见里面放着一握髯与四粒齿。当王把眼光从金篮转移到育温面上时,育温向跪在后面的少女看了一下,说道:“这是某的妻……就是回教皇的爱女。”
埃曼达公主不安似地把头垂下了。王快活地俯视着他们俩说:“只要圆满地做完了那三件事,卿的生命是没有关系的了。不,不,对于今天的出众的武艺,非有赏赐不可。朕愿安卿旧封!”
* * *
育温怎么会忽然到比武场中来的呢?说是这样的:阿倍隆虽安坐在妖精国里,却能晓得天下的事情;因为他想使育温显出惊人的武艺来,所以用白银车把他送到比武场中去的。


